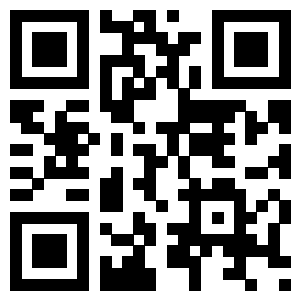強國會士 | 郭孔輝:老院士的新創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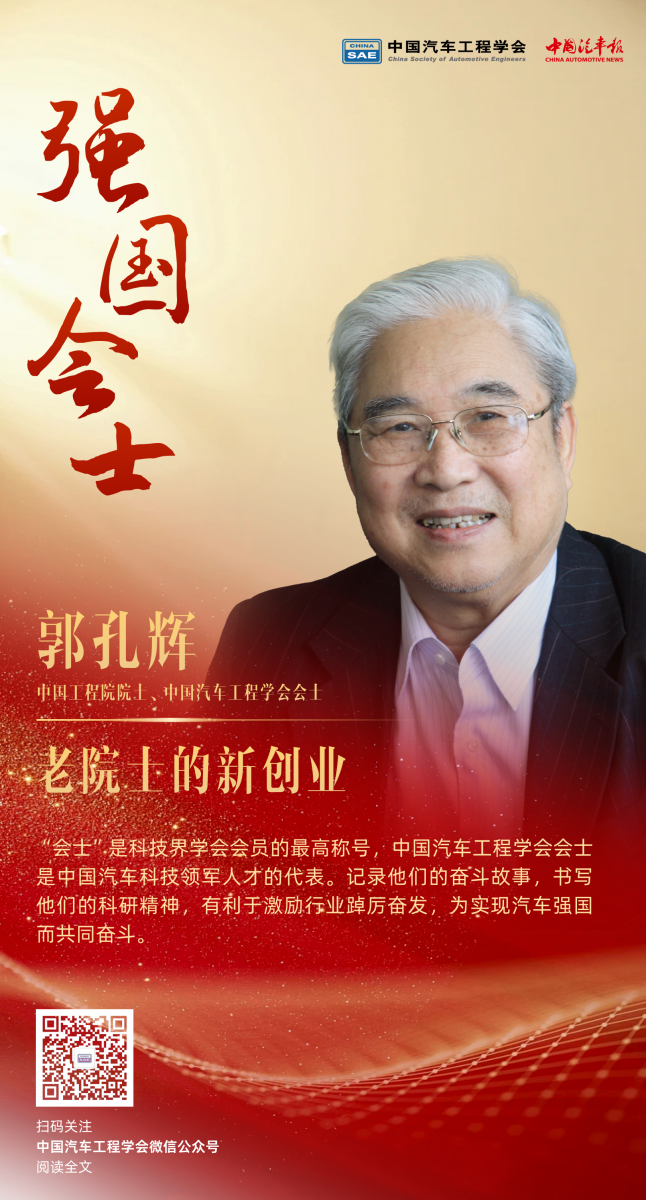
編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會士”是科技界學會會員的最高稱號,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會士是中國汽車科技領軍人才的代表。記錄他們的奮斗故事,書寫他們的科研精神,有利于激勵行業踔厲奮發,為實現汽車強國而共同奮斗。
為什么要創造企業?
很多人是為了賺錢獲利,境界更高的,是為了生產出改善人類生活方式的產品。其中包括科學家創業,為了讓前沿技術能夠產業化,走出實驗室,為人所用。
然而,有一位在創業的老院士,他的目的跟正常邏輯不太一樣。他辦企業賺錢,是為了反哺科研,能讓他無后顧之憂地待在實驗室里。
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重要嗎?重要的是,蛋生雞后,可以繼續孵蛋。
這肯定不是“企業家精神”,但卻是一種“科學家精神”。
轉型
這位正在進行新創業的老院士,就是郭孔輝,我國第一位汽車領域院士。他在2007年創辦的公司叫長春孔輝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簡稱“孔輝科技”),這兩年也逐漸有名起來,隨著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的崛起,成為做空氣懸架的龍頭企業。
“您當時為什么要大聲疾呼,中國汽車產業必須發展自主品牌?”記者問他,“那時候,這個觀點可是很小眾,會被不少人駁斥的。”
2024年春天,記者來到郭院士在長春的家里,回顧起了19年前的采訪往事。當年,因為報道了他的這個觀點,稿子引起不小反響。89歲的老院士,坐在北國春城午后的春和景明中,瞇起眼睛,緩緩地說:“因為我想搞科研,不發展自主品牌,中國人哪有做研發的機會?我們還要從日本、德國進口技術,我咽不下這口氣。”記者以為,他會先說國計民生,結果他卻先說科研理想。
近20年后,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伴隨著“換道”于新能源和智能網聯,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強勢崛起,汽車產業取得了系統性成就,“中國人要做研發的機會”里含著微言大義。
而那時不一樣,就連某部級領導都試圖說服郭孔輝:搞自主品牌不現實,銷售規模小,配套成本降不下來……但他沒看到,只有自主品牌整車發展起來了,自主的配套企業才有市場,才能帶動自主研發,才能讓消費者享受性價比更高的產品,才能讓中國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發揮空間。這是個體系呀!要不,各強國為啥都重視汽車產業呢?
在這個產業邏輯和時代背景下,這幾年郭孔輝和他的公司一起,實現了“轉型”,實現了“逆襲”。郭院士在成為企業的郭董事長后,終于又成功地“降級”為公司前瞻技術部負責人。這個“降級”讓郭孔輝感到無比欣慰——實現了初衷。
選擇
在東北生活了68年的郭孔輝,是福建人。汽車圈一直津津樂道于他的家庭背景:酒店大王、亞洲糖王郭鶴年,是他的堂叔;作為郭氏家族子弟,幾次拒絕了父母要求他出國團聚并繼承家業的召喚,留在國內搞科研;他從小生活的心遠廬,現在已經成了郭宅博物館……
記者打趣他:“您是不是有經商的基因呀?”郭院士笑著說:“這個基因可沒怎么繼承,我適合搞科研。”1952年,這個華僑富商的后代,考上了清華大學航空專業,大二該專業并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大三因有海外關系,轉到了華中工學院汽車拖拉機系,該系后來并入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現吉林大學),1956年畢業后成為一名汽車技術科研工作者。兩年后,隨著一機部北京汽車拖拉機研究所的一分為二,他隨汽車研究所來到長春,從此扎根在這片中國汽車的發源地,一生執著于汽車懸架設計與振動研究。
“您培養這么多學生,最看重他們的什么品質?”記者問。“首先,得有理想,有家國情懷,不能說學習只是為了找個工作。”他說。畢業不久,郭孔輝的父母從馬來西亞回國,希望他能出國團聚并繼承家業,而他卻選擇了留在國內繼續從事汽車技術研究,這個選擇最終成就了中國汽車行業的第一位院士,也成就了今天的一家獨角獸企業。
但其實,彼時那個拒絕成為“富二代”的年輕科技工作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工作并不順利。
“在計劃經濟下,解放牌卡車一車難求,沒有改型的需求,30年一貫制。這種情況下,汽車研發人員能有什么事做?”他說。所以,從1956年開始搞空氣懸架研究的郭孔輝,只能幫助北京無軌電車進行改造,卻也“好景不長”,項目很快下馬。之后,國家進入特殊時期,郭孔輝過上了一邊挨批斗寫檢查,一邊沒有樣車只靠看資料做研究的日子。
一個國家不把精力放在科研上,在國際上早晚要丟臉、要被動。上世紀70年代初,為國家領導人服務的紅旗車無法高速行駛,導致在國外遠落后于其他國家的車隊,數學、力學基礎都比較好的郭孔輝被要求“放下思想包袱”,上陣解決問題。他帶領團隊,在沒有標準試驗場地的情況下,以創新的方法解決了高速操縱穩定性評價問題。同時,也因此進入了輪胎力學的研究領域,并幫助紅旗的新款車774研究轉向與懸架問題,幫助解放141解決擺振、方向盤轉向沉重問題。
車輪擺振、輪胎力學,操縱穩定性、行駛平順性,這些都與底盤、懸架有關。穿越艱難時期,堅持在有限的條件下沿著一條脈絡研究不輟,這些耐住寂寞的時光,陪伴了中國汽車工業的成長。
創業
真正的科學家,總是會選擇那些能全身心投入到前瞻技術、基礎技術研究中的機會。
1993年,在吉林工業大學(后并入吉林大學)校長兩度發出邀請之后,郭孔輝調入高校工作。第二年,他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即便后來當了副校長,我還是希望少做行政,安心科研。”他說,“我帶領建立了國家重點實驗室,集中精力研究操控穩定性。”
然而,即便在大學里,郭孔輝的科研工作依然面臨很多掣肘。比如,爭取到了科研經費,想使用卻非常困難;要安裝大型試驗臺,學校沒有合適場地;想招更多科研人員,囿于編制無法實現。“學生建議辦個公司,用市場的辦法來破解這些難題。”郭孔輝回憶。于是,2007年長春孔輝科技成立了,目的就是方便搞科研、賺錢養科研。
這真是一次初心獨特的創業。公司先從擅長的事做起,賣K&C試驗臺。那時候,只有國外能做這種試驗臺且售價昂貴,而郭孔輝團隊為了能進行底盤和懸架研究,先自主研發出了試驗臺的國產替代方案。賣試驗臺的成果是顯著的:由于有做試驗設備的基礎,對底盤的理解更深了;賺到錢之后,停滯多年的空氣懸架研究重新開始了;后來在向新能源汽車轉型的過程中,這種試驗設備為中國企業提供了不少助力。
“我們的優勢是,有長期做科研的基礎,做試驗設備的基礎,還有吉林大學源源不斷的博士生。”郭孔輝說,“這種產學研一體化的優勢,別的企業不太容易有。”
即便有這些優勢,孔輝科技在創業的頭10年,依然“有上頓沒下頓地找飯吃”。科學家創業有很多“不擅長”,比如,協調各方面關系,“最大的短板就是做銷售”。以及,那種總是從科研角度想問題的思維方式。
科學家精神,用在經營企業上,不靈。
回歸
好在,兒子郭川有郭氏家族的商業思維。更幸運的是,在孔輝科技做足了技術積累后,中國汽車產業發生了劇變。
在幾十年的科研之路上,郭孔輝其實經常“不合時宜”。青年時期,因計劃經濟下汽車不需要改款換型而無事可做;沒有私人汽車消費,舒適度更好的空氣懸架項目被下馬;中年時期,合資企業在中國是主流,他為本土研發人員無用武之地鳴不平;自主整車品牌弱,作為自主供應商難生存。
然而,在創業10年后,80多歲的郭院士有了新機會。“這些年中國汽車產業發展得快,就是因為開放和創新。”郭孔輝說,“電動化使汽車的承載系統發生很大改變,造車新勢力出現了,同時中國汽車品牌開始高端化了。”電動化車型賣得多了,使空氣懸架得以廣泛應用;造車新勢力多了,使本土供應商獲得更多機會;中國品牌高端化了,才能容納空氣懸架帶來的成本。2018年,郭川把公司遷到了浙江,長春孔輝有了浙江孔輝這個子公司,一舉打開市場。如今,孔輝科技已經占有國內空氣懸架市場半數以上的份額,成了獨角獸企業。
雖然上陣父子兵,但科學家父親和企業家兒子一起創業,產生摩擦是必然。
有一次,要做前瞻性研究的郭孔輝要買一輛試驗用車,郭川卻因企業經營成本問題而沒同意,父子之間鬧了別扭。“我們吵架,經常是因為‘遠、近’問題。”郭孔輝說,“我主要關心技術能否成長、能否領先,他更關心公司的效益、收入。”雖然這樣說,郭孔輝其實十分贊賞兒子,也很樂意看到公司發展起來之后,他能安心回歸科研。
以前郭孔輝是董事長,現在郭川當了董事長;以前長春孔輝是母公司,現在浙江孔輝成了總公司。“您是‘降職’為研究院院長了嗎?”記者問。“不,我連院長都沒當上,他有管產品研發的團隊。我負責長春孔輝,做前瞻技術和試驗設備,我管未來。”郭孔輝笑瞇瞇地回答他的新職位,“必須要在技術上保持領先!”
在產業轉型的年代,很多工程技術人員掉隊了,而年紀這么大的郭院士不僅站在了產業發展前沿,還能成功地新創業,為什么?郭孔輝說,他非常重視學生的學術基礎,“未來產業還會發生很大變化,基礎好才能有真正的創新,才能做出顛覆性創新的研究,無論遇到什么變化都能跟上。”他說,“要腳踏實地地做對產業有利的事兒。”
近90歲的老院士,可能是為數不多在公司里職位“越來越低”,卻終于實現了初心的創始人。現在,他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科研了,“我的新技術,不告訴你。”他神秘地說。
來源:中國汽車報 作者:胡軼坤
-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