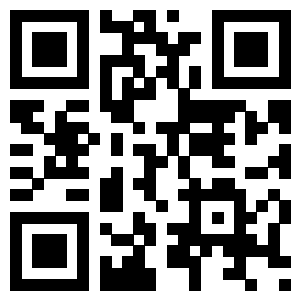強國會士|李開國:我從天空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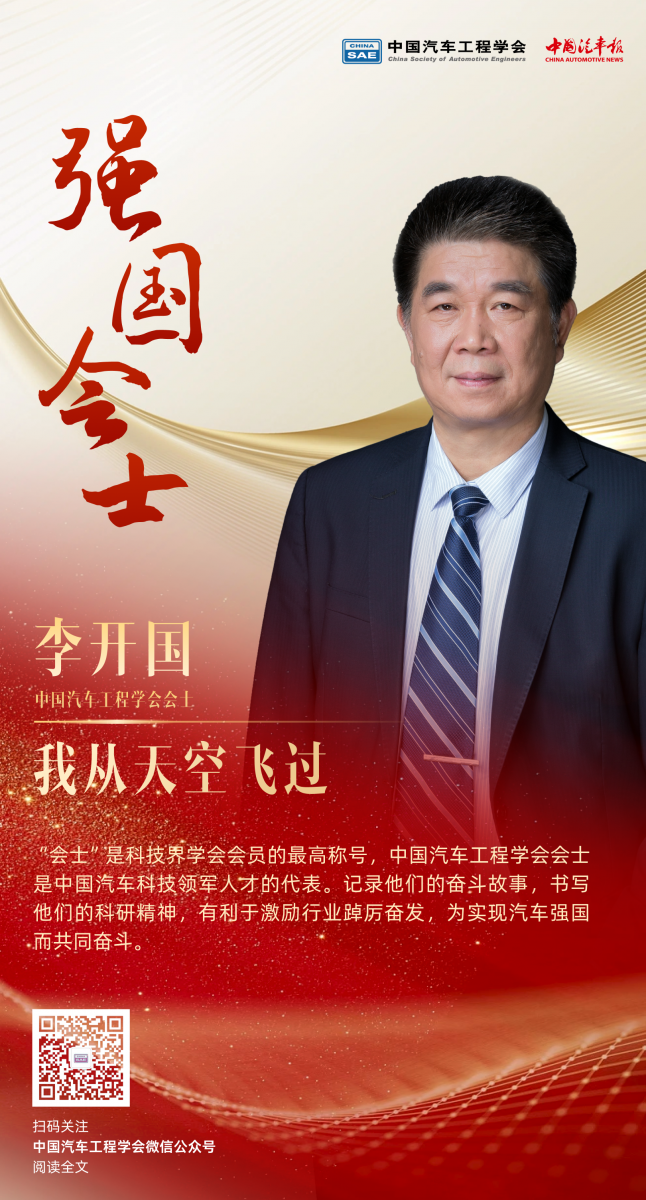
與時代留痕的工程師
“泰戈爾說過,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但我已經飛過。”即將退休的董事長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因年齡的原因,得和大家道別了……”聽眾中有人悄悄濕了眼眶。
2022年5月,李開國從中國汽車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汽研”)退休了,自1983年到重慶汽車研究所開始,他在這里工作了39年,從一名普通工程師到副所長到董事長。“這是我工作旅程的全部,一輩子只干了一個單位,只干了一個行業。”
兩年后,他在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忙著開“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技術路線圖3.0”的專家組會議,除了要負責“節能”部分外,統籌整個路線圖的重任又壓在了肩上。此外,他還擔任著商用車碳中和協同創新平臺專家委員會主任、主持電動汽車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工作。
“到65歲就不干了,我愛玩,要享受生活。”他堅定地憧憬著,卻引起了大家歡快的笑聲。這個美好愿望與他現在的狀態差距有點大,令人覺得兩三年內難以實現。作為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監事長,他今年半年就飛行超過50次,全年下來甚至比當董事長的時候飛得還多,“行業的事兒到年底會更忙。”
他談起自己,總是讓人感覺跟實際情況有點矛盾:忙這么多事兒,幾句就概括完了,還要反問一句:“是不是很簡單?!”同樣,在過去40多年中,他在一線做過技術攻關創新,又在管理崗位上工作了23年,進而退休后為行業的技術戰略服務,他卻總結:“本質上,我就是個工程師。”
南美的蝴蝶扇動翅膀,可能會引發美國的龍卷風。鳥兒飛過天空,當然會為這個世界留下痕跡。
“都說要做時間的朋友,但我覺得要做時代的朋友。”他說。李開國是一個與中國汽車工業近40年發展同頻奮斗的汽車“技術工程師”,是一個領導過行業重要工程研究機構的“企業工程師”,也成為了統籌行業技術戰略協同的“戰略工程師”。這40年,一個工程師的進階之路,定會留下與時代同在的痕跡,就像排云而上的晴空一鶴,遼闊高遠的天空會與凌云翱翔之鳥相互映襯。
“我不是學發動機的”
與專攻一個細分領域的工程師不一樣,李開國經歷了3次行業內的跨領域轉型。“很多人認為我是學發動機的,其實我是個不懂的孩子。”他說,“汽車的很多領域我都經歷過,這跟只在教科書上學的感悟不一樣,理解得更實在,沒有教訓的經驗很難成為經驗。”
第一個教訓和經驗來自人生的第一個課題。1983年,李開國從湖南大學汽車系畢業到中國重汽工作,很快被派往重慶汽車研究所學習,在部件室搞制動研究,這一學習就是3年,最終李開國徹底留了下來。到重慶的第二年,他拿到了“商用車的制動間隙自動調整臂”項目。雖然歷經4年,在5個省份跑了12萬公里的道路試驗,填補了國內技術空白,“但很遺憾,這個課題太超前了。”他說。雖然當時這個技術在國際上已經得到應用,但當時在中國一輛商用車要為此增加300元成本,無法實現產業化。事實上,到了2010年中國市場才大規模應用該技術。“不能只為了搞科研創新而科研創新,當勇士而不要當烈士,這是我從這個項目里得到的重要結論。”李開國說。當然,這個項目也為李開國帶來了人生的第一個汽車科技進步獎。
遺憾和經驗,滋養出了一次成功的轉型。李開國做了制動組組長,又成為固件室主任,底盤、轉向、傳動的工作都涉及到了。通過參與引進日本五十鈴技術的工作,接觸到了日本汽車標準,并且發現中國沒有相應的檢測裝備。于是,李開國帶著七八個人開始了自主設備的開發,把整個真空助力器的測試評價、裝備,實驗室和生產線上用的都成套開發出來了,大幅提升了國內的制動系統測試設備水平。李開國課題組的經驗在所里推廣后,轉向系統、傳動系統也分別跟上,1993年重慶汽車研究所將這塊業務打包成立公司,現在既出口也為跨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汽車設備公司。這個從項目到公司的孵化過程,實現了李開國將技術創新產業化、商業化的理想。此時,他不再是個單純的技術工程師,而是成為了一名總經理。
成為發動機專家,李開國是“被迫”的。1999年在部件室主任和設備中心總經理崗位上干得風生水起的李開國,被調去負責天然氣發動機的開發,因為“搞制動的懂閥門,而閥門對天然氣發動機很重要”。天然氣發動機里有減壓器、閥門、控制器、噴嘴等等,很多事情都不熟悉,先做產品形圖,再制定產品開發時序,從帶著4個人的隊伍開始一干就是8年,從無到有把減壓器、閥門、控制器、標定系統都做了出來,技術成了體系,隊伍也成了體系,項目又成了公司,現在已經占中國天然氣部件市場42%的份額。同時,這個公司也在向氫發動機、氫燃料電池上轉型。“過程中很多艱辛,創新成功有掌聲,但其實在創新中更多的是挫折打擊,甚至是痛苦和誤解。”李開國說。至此,他已經成為一名發動機專家、汽車節能專家,也有了管理經驗。
“我是個輕松的董事長”
工程師帶領團隊攻克項目,有時像將軍一樣在戰場上應對復雜環境,指揮千軍萬馬協同作戰。“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李開國在實踐中學習到,與汽車巨頭合作,意義不僅在于收獲訂單,更在于提供服務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自己無法解決棘手的難題,可以從世界各地尋找資源、引進老師。
“工程應用、工具掌握、采標遵規、環境適應、繼承發展、學科相融、知識更新、交流歸納,工程師應該具備這八種能力。”他把這些從技術攻關到商品落地的經驗總結出來,言語雖然樸素,卻吸引得清華大學的博士生們津津有味地從晚上7點聽到了11點。
善于思考和總結,是李開國對自己的評價,“我是金牛座”。在戰略方法上思考成熟再做事,總結經驗教訓持續進階,這也是能經營好企業的一把手該具備的素質。
不過,讓李開國講幾個在管理崗位上的故事,真是太難了。因為,他太喜歡當工程師。2000年被提拔為副所長時,他拖了一個月才去上任,成為總經理也是因為組織要求“服從安排”。“管理很簡單,就是讓干事的人有權力、讓成事的人有效益。”他說,“做個‘河圖畫家’。”企業是一條河,由若干個小溪組成,每條小溪的水質、流向都掌握;企業是一張圖,刻畫在管理者的腦海中,時刻牢記住;企業是一幅畫,畫好戰略藍圖,講好發展故事;企業就會成為——好好的一家人。
“我是個輕松的董事長。”他說,可是他又說:“我還是喜歡做工程師,有成就感、獲得感。其實我不非常適合做管理,但管理又耽誤了我半生的精力。”故事沒講出來,數據可以說話:在2013年成為中國汽研的總經理后,他帶領這個上市公司實現了10年復合增長率14%。
“技術戰略得適合中國人”
李開國從2006年開始參與行業技術戰略工作,正是由于他轉型成為了發動機專家,被委任為國家“863”計劃重點項目“汽車開發先進技術”專家組組長。他當時提出了“兩車、兩機、兩箱”的技術戰略,即推動商用車和轎車的正向開發體系化技術,開發一款10升以上的柴油機和一款1.5升的缸內直噴汽油機,并提倡轎車主抓DCT變速器、重型車走AMT的技術路線。
做工程師最單純;成為企業管理者,免不了要承受委屈;做行業技術戰略統籌人,更需要時刻面對議論和質疑。DCT變速器的技術路線,一度成為行業熱門爭議話題,李開國當時壓力非常大。“但我始終有一個信念:要選適合中國人的技術路線!”李開國說,“AT有美國和日本的技術壁壘,我國高精度行星排的制造水平也不行,但MT基礎非常好,適合在此基礎上做DCT、AMT。”現在看,DCT已經成為中國品牌主流整車企業的普遍戰略選擇,也為混動、電動技術的拓展打下了基礎。李開國覺得,曾為此持續48小時不睡覺地工作是值得的。
2008年,李開國又成為國家發改委節能路線政策中替代能源天然氣專家組的組長;再后來,他就成了“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技術路線路”1.0、2.0和即將出來的3.0的更重要參與者,乃至統籌人。去年他公開判斷,傳統能源內燃機仍將是商用車重要技術路線,柴油機熱效率將最高可達55%,天然氣、甲醇內燃機熱效率逐步趨向于柴油機水平;2025年后HEV技術開始普及,能耗降幅會在2040年達到35%以上;氫內燃機在2025年左右達到量產條件;純電動商用車將在2030年在公共領域及中短途場景實現產業化應用,滲透率有望突破50%。
現在,距離世界主要汽車生產國都關注的“路線圖3.0”發布只有5個月了,李開國的統籌工作相當繁重。以前,我們可以參照發達國家,而現在中國汽車已進入原始創新狀態,沒有參照系了,甚至還要為別人提供參考,技術戰略的制定就更難了。“統籌人不僅要進行技術分辨,還要進行中間技術的鏈接。”李開國說,“這是最難的,因為人都有屬性,每個技術群體都想將自己做大,但我們要保證體系性。”
看來,做行業的“技術戰略工程師”,也不比做管理一家公司的“企業工程師”輕松。即便李開國退休之后來中國汽車工程學會,要求“不管人、不管事、不坐班”,但也沒法“享受生活”。這是一只注定還不能停歇的鳥兒,他覺得:“我是幸運的,我是欣慰的,我是收獲的,我是堅守的。” 這樣的痕跡,已經足夠絢爛。
來源:中國汽車報 作者:胡軼坤

- 大家都在看